湾区装修与庭院施工,联系:rizuo-com(去掉-,微信同号)
为什么你的家可能掌握着你依恋风格的线索?
![图片[1]_童年创伤与室内设计之间不太可能的联系_日作设计](http://rizuo.com/wp-content/uploads/2021/10/1-1-755x1024.jpeg?v=1634466445)
1989年,当我父母完成离婚手续时,爸爸签了一份需要铺设新地毯的公寓的租约。他向房东强调了地毯是红色的。
那份租约最终失败了。相反,他搬进了一个铺着米色地毯的一居室复式公寓,并买了一张红色金属双层床。他睡在下面,我睡在上面。
每年的圣诞节,他只要求我送他一块红色的肥皂。他的毛巾是红色的。他的床单是红色的。他的毛衣。
红色对我的黑发和苍白的肤色有很好的作用。但直到最近,我很少穿它。它是权力的颜色,是工作面试和热辣约会的东西,是口红和注意力。
它也是我父亲盲目愤怒和我童年创伤的颜色。
在我15岁之前,我每隔一个周末都和他呆在一起。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原子都有香烟的味道。我无处可去寻求解脱。但我还是把头埋在毯子里睡觉。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幻想着把他的阁楼改造成我自己的房间。通过拉绳的折叠梯子进入,它直接开在浴室门前。
我当时太年轻了,不明白那些有租约、有房东、有可卡因瘾、有蓝领工作、有自己的创伤性童年的父亲是不会为他们的女儿装修阁楼的。
不过,我还是想象着一张双人床,日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书架上摆着书。我不需要空调;我只想能关上一扇门,把自己封闭起来,防止周一他把我送到学校时我身上的臭味。我想要一个逃生舱口。
我对室内设计的兴趣始于高中时代。我的一篇日记中描述了我把我的卧室漆成墨蓝色,并描述了它是多么让我高兴。
颜色,特别是,让我着迷。在现场,我可以说出许多品牌的油漆颜色。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的墙壁上特定的白色阴影的名称,但不保证。
我最终成为了一名作家,而不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我通过尽可能多地写关于设计的文章来弥补这一差异。
在最近的一次任务中,我通过Zoom采访了设计心理学家Amber Dunford。她描述颜色时,就像厨师描述一种味道一样津津有味。她说,她最喜欢用绿色来装饰,是那些 “水样 “或 “深色和植物 “的绿色。
在那次采访中,Amber不知不觉地给了我一份礼物,她把在我父亲家的那些漫长的沉闷的周末和我长期以来专注于使我周围的一切变得漂亮联系起来。
除了设计你在Overstock.com上看到的套装,Amber还教授她自己创造的大学课程,探究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空间之间的关系。
她解释说:”过去从你的童年开始对空间的依恋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零到五岁是你依附于另一个人的形成期。这是你如何运作的蓝图。根据你的情况,它为你在成年生活中如何依附于人着色。
依恋理论是我最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一个行为系统已经进化到使婴儿接近他们的照顾者,免受伤害。婴儿要么以焦虑、回避或安全的方式与他们的照顾者发生关系(后者是理想的依恋)。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些依恋类型就像宝丽来照片一样在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或我们希望被爱的人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心理学101课程中听说过依恋理论,然后很快就把它忘了。也许我们还不关心为什么我们的童年会把我们搞得一团糟,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此外,这个故事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故事。它涉及科学家和20世纪60年代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实验室、护理人员、玩具、将幼儿介绍给陌生人并评估他们的反应。还有一位名叫玛丽-安斯沃斯的女先驱。
我不熟悉的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如何长大,或与谁一起长大,而是在哪里塑造了我们的关系方式。房子、空间和地方–无论是我们漂流过的地方还是我们居住的地方–都有办法进入我们的神经系统。
“当我们走进一个空间,”Amber说,”我们立即有一种感觉,无论你是否认识到这种感觉。空间对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情绪健康具有影响力。它们可以使我们感到轻松;它们可以使我们感到焦虑。我教人们如何利用这一点–无论是他们自己对空间的依恋,还是他们在童年时的空间历史。有些人重新创造混乱的空间,因为他们熟悉它们,即使他们知道它们并不那么健康。某物的气味,或某物的感觉,或风景,或一个地方的布局,都可以有怀旧的记忆,如果你在你的成年生活中重现它们,就会感到非常平静。”
蓝色和绿色一直是我的主打产品。我也曾对黄色、粉色和紫色有过迷恋。我曾经花了很多天在楼梯间的地板上画金箔玫瑰花。但我从来不喜欢用红色装饰。
现在我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潜意识中出现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一直影响着我的大脑、心脏和神经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人有关,但也与红色有关。还有双层床。
我每隔一个周末在父亲家经历的忽视和愤怒,几乎可以解释我现在对其他人的不关注和愤怒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神经系统会以这样的方式记录威胁,以至于遇到前男友的时候,我就像遇到车祸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有双层床的小屋或海滨别墅度假时,我都会从那个房间里退缩。
有一天早上,我父亲叫醒我,告诉我戴安娜王妃去世了,当时我快15岁了。那时,他已经在这栋复式楼里住了很久,墙壁已经变得和厨房里的油毡一样黄。油漆从墙上剥落下来。冷凝水沿着窗外的空调器结成水珠。
这些年来,我在红色的双层床里多次问我父亲,他能不能不打鼾。这总是会激怒他。我还问过他,请他关掉那台带兔耳天线的小电视机发出的呻吟声。
“睡觉吧,艾伦,”他吼道。但我从来没有做到。
电视机开着,告诉我们关于戴安娜的新闻。话说回来,电视总是开着的。
我起床后给他做了早餐。我总是这样做。
我并不关心戴安娜。但他关心。
她死后几个月,他最后一次对我发火。他的汽车收音机坏了。他试图用车里的吊箱播放弗兰克-辛纳屈的磁带。但吊箱的电池没电了,所以他把吊箱扔到后座上,其凶猛程度让我感到恐惧。
当我对他的爆发提出抗议时,他让我滚出他的车。
我走了几英里回到他的复式公寓,到达时满腔怒火。当他从前门走出来,懊悔不已时,我告诉他,他可以去操他自己。
我再也没有在那里住过一晚上。
在我最常做的一个梦中,我买了一座老房子。之后,我才发现了一扇秘密的门,它通向一个比房子本身大得多的侧翼。找到它我很高兴。这里有挂满灰尘的大楼梯,有一间又一间被保留下来的卧室,有坟墓般的浴室,我已经计划对其进行翻新。
我想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美好。在我的梦想中,我可以。这将是我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使命。
这些天来,我对红色的态度更加平静。我现在把我的脚撑在一个老红色谷仓颜色的箱子上。我带着一个红色的钱包。我穿红色的衣服。
我已经明白为什么戴安娜的死是一个全球性的悲剧,为什么她的敏感性是如此精致,如此非凡。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双层床让我感到不舒服,即使他仍然睡在我们的床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踏进他的住处了。
上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床漂白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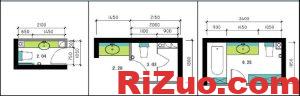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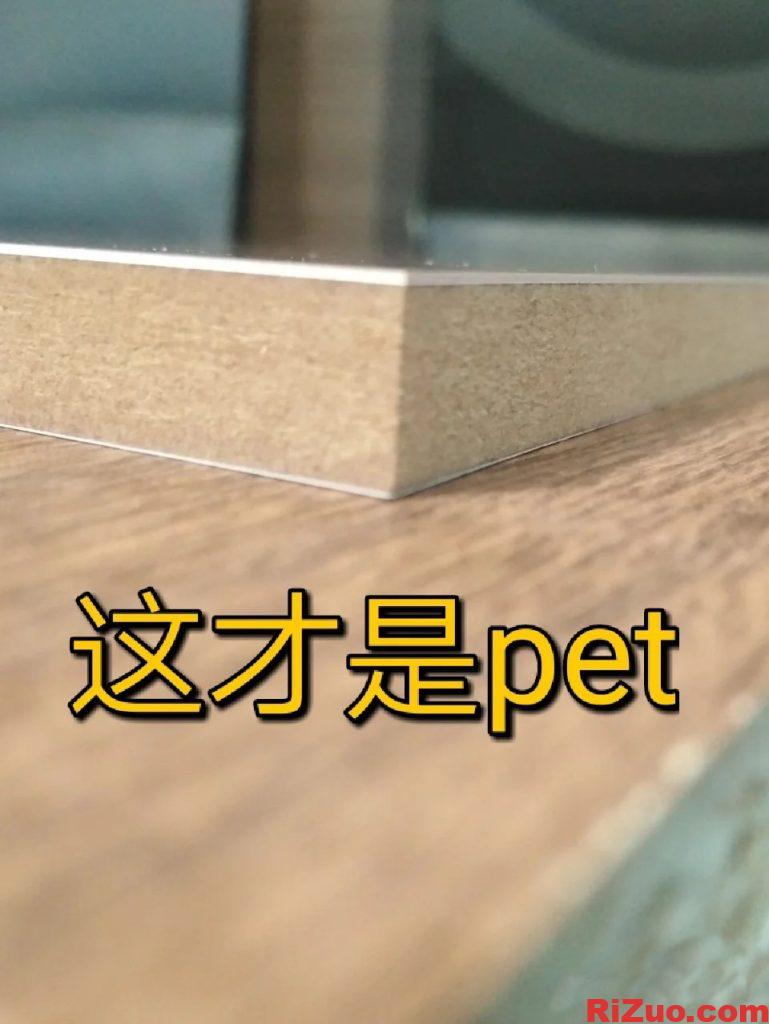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